我們的雙手深入病患的軀體,用戀人無法做到的方式撫摸他們。
我們用手指破開感染性腔室薄弱的網狀隔膜,用圈成杯狀的手掌將凝固的血塊舀出來,以隔著手套的指甲將一圈圈黏連的腸道剝離。
我們的工作是自我的延伸,但是我們卻進一步相信——我們「等同於」我們的工作。
罹患先天疾病的男嬰麥克斯,接受了肝臟與小腸移植。在主治醫師「拯救生命」的狂熱意志驅使下,十個月大的男嬰前後十度被送進開刀房,直到身上找不到一小塊可以穿過縫線的完好皮膚。
三十歲的巴比膽管長了巨大腫瘤,術後癌症復發且癌細胞快速擴散,但病人和家屬不曾被告知「真相」,他們始終對病情樂觀以對——直至巴比在加護病房被強烈急救、壓迫、重搥,度過生命的最後幾個鐘頭。
外科醫師溫柔地領婦人進加護病房,握住婦人的手,輕聲解釋正在發生的事。婦人哭倒在丈夫床前。醫師拉上床簾,將他們三人圍在裡面。醫師低聲在婦人耳邊說話,接著,把自己的手放在病人的手臂上。
如同所有醫學院學生,作者在大體解剖課上,初次體驗「面對死亡」的啟蒙儀式;這時她才明白,儘管抱著拯救生命的夢想,進入這一行卻得與死亡為伍。她從老師和醫界同僚那裡學到,抽離情感、否定自身的感受,便能暫且調適對死亡的焦慮。這是十餘年的醫學院課程與訓練,教給新進醫生的諸多「成規」或「非正式課程」之一。
「成規」教導醫生把複雜的臨床問題抽絲剝繭、化繁為簡,卻在「解構」難題的同時,忽略了人性的「連結」;使得醫者聚焦於「治療」之餘,往往忽視了心靈與肉體的關係、醫生與病人的關係,以及人性與疾病的關係。
醫生是生命最終的監護者,引領著病患和家屬,走過通往終點的艱難路段。而醫生能否在病患的生命終點,提供真誠的關懷與支持,如同醫者所面對最嚴峻的「最後期末考」。
作者追溯自己的求學與訓練過程,探討現今的醫學教育如何過度偏重「克服死亡」的知識,卻抹煞了病患的人性面,使醫者對死亡的疑懼一再在醫界複製繁衍;導致醫生不自覺地從瀕死病患身邊逃開,或無法開口和病人及家屬討論不樂觀的病情。當醫者深入理解自身「死亡焦慮」的根源,以及「治療」的意義(更多的治療,並不代表更多的「愛」),才能做某些比「治癒疾病」更重要的事:陪伴在病患和家屬身邊、聆聽他們的感受、紓解他們的傷痛。唯有如此,醫者才能成為真正的「療癒者」。
Pauline W. Chen(陳葆琳)
在美國出生成長,父母來自台灣。畢業於哈佛大學及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,其後在耶魯大學、美國國家癌症醫院,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(UCLA)完成外科訓練;後長期任職於 UCLA醫院,專攻肝臟移植。1999年,陳醫師獲選為 UCLA 年度傑出醫師。 陳醫師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專文〈死透了嗎?腦死的矛盾〉(Dead Enough? The Paradox of Brain Death),名列2006年美國國家期刊獎決選名單。2008年11月,陳醫師獲美洲中華醫學會(CAMS)選為「傑出公眾服務獎」得主。由於《最後期末考》英文版頗受讀者好評,陳醫師應邀為《紐約時報電子報健康版》(
www.nytimes.com/health/
)撰寫專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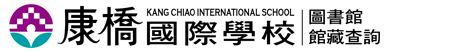
 借閱次數
:
借閱次數
: 